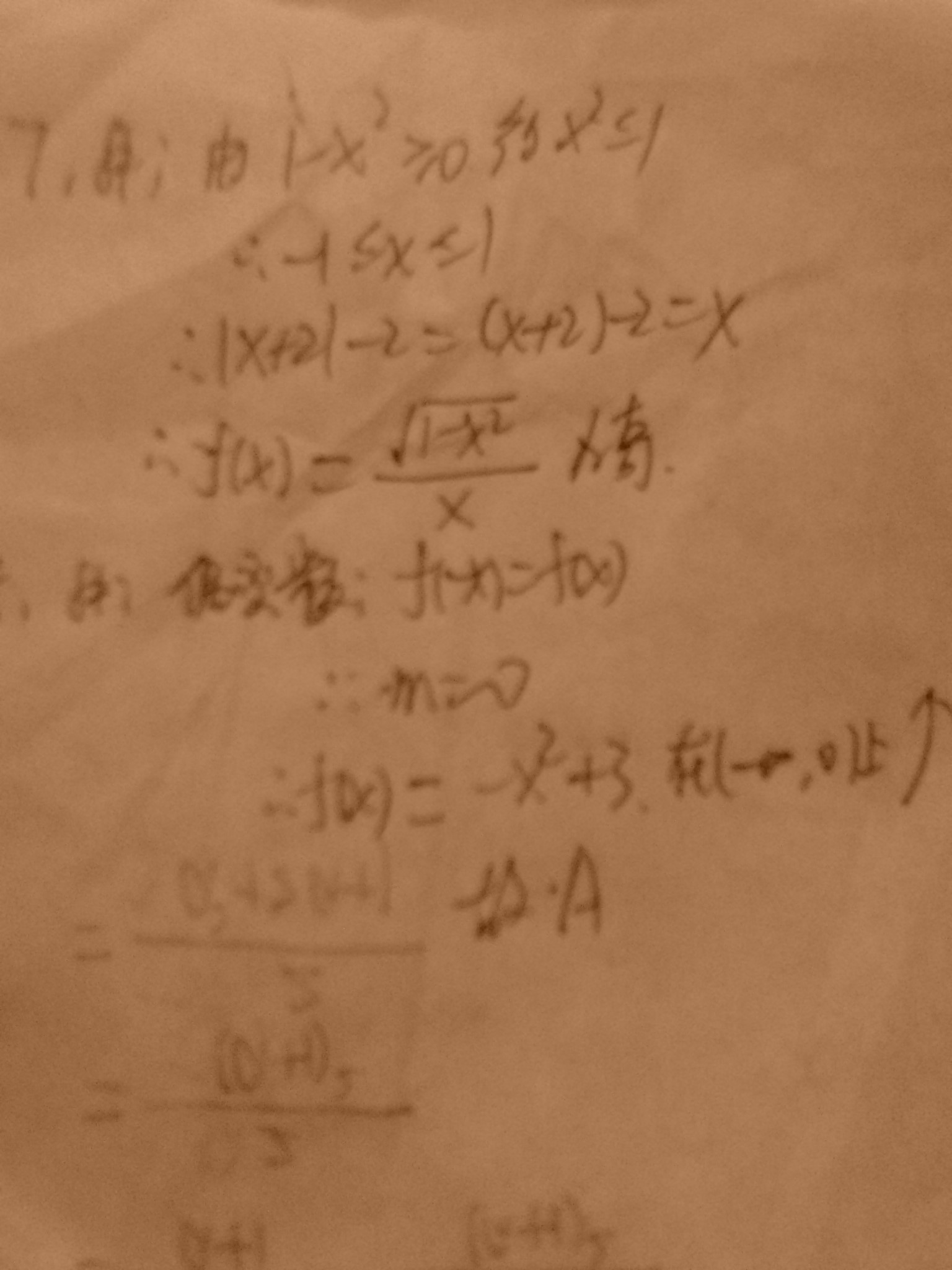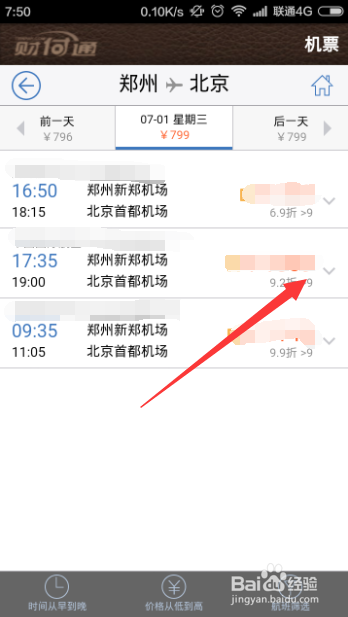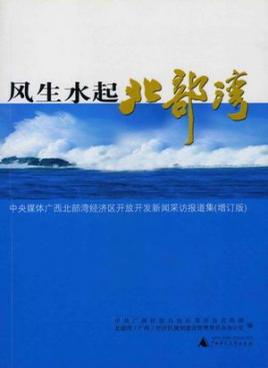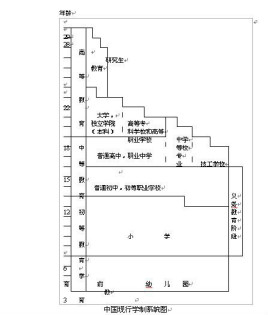一、叔本华:“世界是我的表象”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 年)是最尖锐的黑格尔批评者之一 他是黑格尔的同时代人,但比黑格尔更年轻,他不愿意被黑格尔的巨大名声所胁迫。作为刚开始在柏林大学工作的哲学教师,叔本华将他的课程安排在与黑格尔开课的时间相同,他完全明白,这种做法必然使他自己只有极少数学生。这位自大的年轻哲学家对黑格尔的看法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我们可以从以下他对黑格尔毫不奉承的描述中看出这一点:
他是黑格尔的同时代人,但比黑格尔更年轻,他不愿意被黑格尔的巨大名声所胁迫。作为刚开始在柏林大学工作的哲学教师,叔本华将他的课程安排在与黑格尔开课的时间相同,他完全明白,这种做法必然使他自己只有极少数学生。这位自大的年轻哲学家对黑格尔的看法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我们可以从以下他对黑格尔毫不奉承的描述中看出这一点:
黑格尔,被来自上面的大人物任命为持有证书的“伟大哲学家”,是一个愚蠢的、乏味的、令人作呕的、无知的江湖骗子。他胡编乱写、粗制滥造些故弄玄虚的荒谬废话,其无耻大胆已然登峰造极。
事实上,叔本华只对两位哲学家——柏拉图和康德——表现出深深的敬意。他也赞赏印度的哲学传统。对叔本华而言,纵观历史,所有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饶舌之人”而已。
叔本华开始其工作时要求回到康德,而事实上,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部分根本上来说是对康德思想的复述。叔本华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人类心灵无法认识终极实在,我们能够通过理智把握的唯一实在是穿过了时空之网和知性范畴的实在。叔本华写道:
“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任何一个活着并认识着的事物都有效的,尽管只有人能够将它带入反思的抽象意识。要是人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已经达到了哲学智慧。继而对他来说变得清楚而确定的是他所认识的不是什么太阳或地球,而是一双看见太阳的眼睛,一只感触着地球的手;那个围绕着他的世界只是作为一个表象存在着。
回想一下,当康德提到本体世界的时候,他主张我们无法认识它,尽管基于某些实践上的需要,我们有权对之持有各种信念。我们看到,对于康德来说这些信念是极其乐观主义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对不朽的信仰,以及对永恒正义的信仰。而且,康德还指出某些人类经验,我们的某些直观,康德希望这些可能是关于不可知的本体世界之本性的超理性线索。举个例子,当我们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晚上遥望夜空,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崇高感是存在的。同样让康德深受启发的是我们在某些危急关头所体验到的道德责任感。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有两个东西不断地在心灵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景仰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同样,叔本华也认为存在某些应该留心的直观经验,因为这类经验很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对终极实在的超理性洞见。但叔本华所举的这类例子实际上与康德的迥然不同。
比如,叔本华想知道何以当某个人被告知一个熟人的死讯时,他首先经验到的刺激是咧嘴而笑的冲动——当然,这是必须得到抑制的冲动。叔本华还想知道,一个可能经过积年累月不知疲倦的工作才最终取得成功和权力的受人尊敬的商人或者政府官员,为什么会愿意用所有这一切冒险,只为与一个被禁止(与其发生关系)的伴侣那片刻床笫之欢。这些以及类似的人类经验导致叔本华对终极实在的本性持有比康德悲观得多的直觉。叔本华的阴郁疑虑很快成为他体系中的“真理”。(这些非认识论真理的奇特地位没有逃脱叔本华批评者们的双眼。)叔本华曾说:“‘世界是我的意志’这个真理对每个人来说如果不是可怕的,也必定是非常严重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它是一个人可以说出来、也必须说出来的真理。”
叔本华的可怕真理实际上是这样的:在显象背后,在现象之幕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本体实在;但它远不是康德所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上帝、不朽和正义的良善之地,叔本华在此所发现的是野蛮的、火热的、无情的、无意义的力量,他称之为“意志”。这个力量在其永不满足的对“更多”的要求中创造一切,又毁灭一切。(它不知道要更多的什么东西——它只知道它想要更多。)
理解叔本华的意志概念最好的现象界的意象就是性和暴力。不仅在自然界中,而且甚至在人类领域中,每个事件都是一个产生和毁灭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其动机,事实上都是以某种方式服务于产生和毁灭的行为。如果你熟悉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你现在就能知道他的“本我”观念是从何而来的了。甚至“本我”这个名字(id 这个拉丁文意思是“它”)也和叔本华的“意志”一样表示着本体的不确定性。弗洛伊德本人曾在 1920 年说过:“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驶入叔本华哲学的港湾。”
叔本华认为,现象世界的每一事物都只是这种强硬意志的显示,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一种“意志的对象化”(也就是说,穿过了范畴和时空之网的意志)。
叔本华“意志”的各种意象尽管愚蠢而粗暴,但他也将意志设想为极度狡诈的。意志能够向其自身的“实验”隐藏它的残忍意图,这些“实验”可能会冒犯或甚至会报复意志。换句话说,人类的心灵就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即便在其世界观上也自我欺骗。意志穿过时空网格和范畴时改变了性质。然而,如果我们可以清除我们本性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本身就是意志的狡计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能够看透自然,并且明白除了赤裸裸的生殖需要,它丝毫不关心任何造物的幸福与安康。叔本华通过对南太平洋的巨型海龟的描述来阐述他的观点。巨型海龟在交配期竭力爬到海滩上以便把它们的卵产在沙中,据说,在暴风雨中,数以百计的这种海龟会在岩石海岸边摔得粉身碎骨。叔本华还提醒人们注意一种奇特的蛾类,它们从蛹中一出来就具有完整的生殖和消化系统;但自然却忘了给它一个小零件——一张嘴!所以这种蛾子繁殖后立即去寻找食物,但很快就饥饿而死。但是,自然并不在意,因为这种蛾子已经产下了它的小卵。在叔本华看来,人也跟海龟和蛾子一样。如果你超过了十八岁,那么你的肉体就开始衰退。你的肉体,只不过是生殖系统的脚手架而已,一旦它在适合的位置产下后代并给这些后代一个复制它们自己的机会,就开始死亡。
这个消息确实很可怕。为什么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全都处在非理性的、无意义的意志奴役状态之下呢?原因便在于意志的狡计。人类文明本身只不过是意志的一个又一个实验而已,而人类的乐观和希望也只不过是意志给予我们的礼物而已,这个礼物必然使我们继续在关于真实形势方面欺骗自己。艺术、宗教、法律、道德、科学,甚至哲学也只不过是意志的升华而已,而升华也还是为了意志自身的目的。黑格尔对上层文化的称颂也只不过是对意志绝对胜利的证明。
我们的所有希望和志向都会遭遇破灭。幸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幻。任何一个人随便在哪一天只对报纸看上一眼,之后他还能是乐观主义者,那就太荒谬了。泥石流吞没了整个村庄,一个疯狂刺客的一颗子弹将一个民族的希望击得粉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死于一场痛苦的疾病。战鼓从未停止过敲动,不光彩的死亡在等待着所有人。确实,只有愚人才能在直面这样的真理时还依旧保持乐观。
哲学无疑从来没有像在叔本华这里那样如此沮丧,又令人沮丧。但是,在他看来,他的悲观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悲观主义,而他为这种“理性”的悲观主义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之道。当然,也曾有过其他明白这个真理并为之寻求理性回答的人。在叔本华看来,耶稣和佛陀都曾是悲观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解决之道都是空想,并且依然服务于意志。(除此之外,他们的学说还被意志的狡计所篡改,这一点表现在他们教徒的乐观主义上,信徒们将其先师的悲观主义消息作为“福音”提出来。)柏拉图也曾经提出一种“近乎”成功的解决之道,但是他的永恒“理念”仍然是表象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只是意志的一部分。
似乎叔本华哲学所能提出的唯一劝告应该就是自杀了。但事实上,叔本华却劝告人们反对自杀,他的理由是,自杀是意志最后的孤注一掷,因而仍然是意志的显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行为像自杀一样要求如此多的意志的集中;因而,自杀不可能是对意志的否定)。
切勿绝望!还有一种叔本华式的解决之道。尽管所有文明都只不过是性和暴力的升华,因而只是意志的实验,但文明世界可以达到一个精妙的程度,在这里它可以与它自己的无意识的起源断绝关系,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领域,事实上,这个领域是反自然并且因而是反意志的领域。这种摆脱了意志的自治出现在艺术世界的一个特定角落——即音乐的角落。但并不是所有音乐。流行音乐肯定不行,它所做的正是唤起现象世界的想象和情感。大部分古典音乐也达不到。比如,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想象依然太过强烈;因而它与意志的联系也就太过明显。(当我们聆听《田园》时,我们看到草地上的牛群、嫩绿的青草和野花,还有朵朵白云飘过蓝天。)这样不行,对意志的摆脱只能在对纯形式的音乐的冥想中才能实现,这种音乐没有歌词,也没有想象。有一种巴洛克音乐符合这个标准——一种纯粹数学式的形式主义:主题、复调、主题。一个人有可能尽其一生不计私利地沉思这类音乐。叔本华恰恰提出这种沉思来作为他认为的“涅槃”——从现世脱离,逃入纯粹形式之中,因而战胜了意志。这就是柏拉图和佛陀笨拙地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
叔本华哲学在德语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要是没有叔本华,那么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托马斯·曼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设想的。然而,似乎没有什么人认真地看待叔本华的解决之道。再明显不过的是,正如尼采将要指出的那样,巴洛克音乐是所有音乐中最感性的,而且欲求将自己沉浸于其中,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欲望,因而还是意志的作用。
二、请问这是什么蛾子?吃什么?在屋里一晚上好像快饿死了
糖水。
你没图也不好判断,不过只要知道去吃的话喂糖水没啥问题。蛾子闻到空气里的糖分会自己去吃的,不要把它扔糖水里。
有类似蚕蛾类和大蚕蛾类这样羽化后不吃东西的蛾子。
如果是在屋子里折腾了一晚上,估计没救了。
另外,如果是这样的蛾子
美国白蛾
踩死!这是天灾级的害虫。
三、我字加偏旁组组成字再组词。
我字加偏旁组组成字再组词。俄,俄国;鹅,天鹅;娥,田娥;蛾,蚕蛾;莪,萝莪;峨,天峨;……